凌晨三点,我从梦中惊醒,额头全是汗。梦里,母亲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,坐在老屋的门槛上,手里剥着毛豆,抬头冲我笑。她离开人世已经七年,可那一刻,她的皱纹、她指尖的茧、她呼吸里淡淡的皂角味,全都真实得让我不敢眨眼。醒来后,我盯着天花板问自己:梦到去世的妈妈是什么意思?难道只是大脑随机放电,还是她真的跨越阴阳来见我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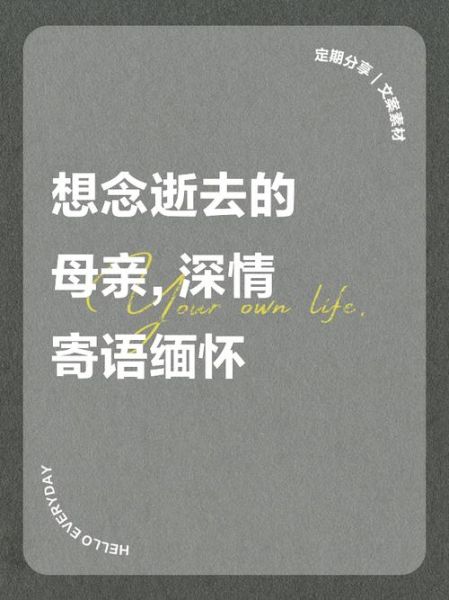
心理学视角:弗洛伊德在《梦的解析》里把“逝者入梦”视为潜意识未完成愿望的投射。母亲去世时,我正漂泊在外,没赶上最后一班车,没见到她最后一面。这份遗憾像一根倒刺,七年里反复发炎。于是大脑在REM睡眠期,把记忆碎片重新剪辑,让母亲“复活”,补偿那场缺席的告别。
民俗学视角:老家老人说,亡人托梦有三类——报平安、诉遗憾、示吉凶。母亲梦里剥毛豆的动作,是她在告诉我“家里后院的豆子熟了,你别忘收”;而她没开口说话,按老一辈的说法,是“阴阳有别,言多泄气”。
步骤:
① 睡前反复默念“今晚我要在梦里拥抱妈妈”;
② 在手腕套一根橡皮筋,白天每看到一次就问自己“我在做梦吗?”——这叫现实检验;
③ 当梦中出现母亲时,捏住自己的鼻子尝试呼吸,若能呼吸即为清明梦,此时可主动与她对话。
准备母亲生前更爱的信纸(或她旧衣剪成的布片),写下三件事:
- 你最后悔没对她做的事
- 你最近最开心的瞬间
- 你希望她为你骄傲的事
写完叠成小船,放进流动的河水或点燃后随风飘散。心理学称之为象征性完成,能显著降低丧亲者的侵入性回忆。
我保留着母亲的顶针。每次手指被纸张划破,就戴上它,像小时候她为我缝校服那样,把伤口贴在顶针的凹痕里。金属的冰凉触感会激活普鲁斯特效应——嗅觉、触觉比视觉更容易打开记忆闸门。此时轻声说“妈,我今天……”,说完会发现喉咙不再发紧。
反复出现的场景:
- 老屋的门槛:象征“过渡”。她去世那年我正好跳槽,门槛是旧生活与新生活的分界线。
- 剥不完的毛豆:毛豆需要一颗颗剥开,对应我这些年“慢慢来”的自我疗愈。
- 她始终不进门:民俗解释为“亡魂不能踏生宅”,心理学则认为是我的防御机制——不让她真正进来,就不用再次面对永别。
自问自答:
Q:为什么梦里母亲从不说话?
A:语言是理性的,而梦是图像的。她沉默时,我反而能更清晰地听见自己内心想说的话。
如果以下情况持续超过一个月,建议寻求哀伤辅导:
- 每周梦见母亲三次以上,且醒来后出现心悸、盗汗;
- 梦中母亲形象扭曲(如腐烂、哭泣流血),伴随强烈罪恶感;
- 白天出现“假性重逢”——在超市货架间突然闻到她的雪花膏味,并产生跟随幻觉。
北京回龙观医院哀伤门诊的干预方案包括:眼动脱敏治疗(EMDR)、空椅技术(对着空椅子扮演母亲对话)、记忆再巩固(在回忆中插入新的积极画面)。
我开始在豆瓣小组“逝者留言板”连载《母亲梦境日记》。第17次记录里,我写道:
“昨夜她带我去看新种的月季,说‘这花叫“女儿红”’。我醒来查资料,发现根本没有这个品种。但三个月后,我在花市真看到一盆标签错写的“女儿红”,买回家当天,它开了七朵花——母亲去世那天,正是农历七月初七。”
现在,这盆月季成了我的“梦境锚点”。每次不确定她是否来过,就数花苞:单数是她来过,双数是我太想她。 irrational?也许。但哀伤本来就不是理性的事。
凌晨四点,我重新躺下。这次不再追问梦的意义,而是轻轻对黑暗说:“妈,下次记得带把剪刀来,后院那棵月季该修枝了。”窗外,风掠过月季的刺,发出细微的“嚓嚓”声,像她生前在厨房磨刀的节拍。
发表评论
暂时没有评论,来抢沙发吧~